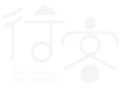我在澳门的时空缝隙里,偷得了一场充满市井的喧嚣
在澳门逗留的时光,路过气势恢宏新葡京娱乐城,也走过威尼斯人灯火通明的娱乐场,也在澳门银河里走了一圈,那些光怪陆离的空间暗涌着深不可测的江湖,而我的兴趣在于市井。
当飞机降落在澳门国际机场时,夜幕已经降临,出机场后,我乘坐一辆开往酒店的大巴,沿途璀璨的灯火和金碧辉煌的建筑,暗示着这座城市的纸醉金迷。
酒店地处澳门娱乐场所聚集区域,距离老城区的闹市还有十几公里。附近的澳门银河等众所周知的场所步行只有5分钟。将行李一股脑放置在酒店房间后,我下楼溜达了一圈。楼下美食街的摊贩热情地招呼我进去用餐,问了一下价格,太贵,一小碗米饭14元,而在北京,也就2元的样子。我只好在便利店买了一盒辛拉面、一个卤蛋、一听啤酒,花了46元,回房间烧了一壶水搞定了晚餐。

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了一辆公交车,去了老城区,我要去看大三巴牌坊。彼时,正值上班高峰,每一个路口都人声的嘈杂,如同潮水,从身后低矮的市井巷陌漫上来,又被前面石阶上更多熙攘的喧哗每一个路口盖过去。
循着导航走街串巷大约20分钟后,当那面巍峨的、被阳光漂得发白的石壁毫无预兆地撞入眼帘时,所有的声音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。不是寂静,而是一种巨大的、有质量的空旷,笼罩下来。它就那么立着,背后是澳门蓝得有些虚幻的天空,像一个过于庞大的、关于历史的华丽墓碑,也像一扇通往虚空的、永远无法再推开的门。
大三巴牌坊,从我知道澳门这座城市那天起,就知道这个牌坊了。可我总觉得,这称呼太轻,载不动它身上层层叠叠的时间。

四百年前,葡萄牙人将一座名为“圣保禄”的教堂立在这山岗上,花岗岩的躯体里,奔流着远东传教的热望与雄心。火光却两次舔舐它的梁木,终于在1835年那场巨焰后,只留下这面倔强的正面前壁,和门前宽阔的、被岁月磨得光滑的68级石阶。
巴洛克式的繁复雕饰里,藏着东方的莲花与汉字,青铜的圣像沉默地俯瞰,那些石雕的魔鬼被天使的长矛刺穿——一种遥远的、属于另一个大陆的叙事,却深深楔入了这座东方小城的骨骼里。
几乎所有来到澳门的人,都要来到大三巴牌坊,那庄严肃穆的历史感里,仿佛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一切记忆。


大三巴牌坊周边是一片老城区的巷弄,有的碎石铺就的小巷窄得只容两三人并肩,缝隙里挤出茸茸的青苔。路是起伏的,顺着山势,时而探向一片开阔,时而又隐入楼宇的阴影。两侧的房屋,色彩被岁月调和成一种温润的调子,鹅黄的墙面剥落了些,露出底下砖红的底色;浅绿的窗框漆皮卷曲,像秋日欲坠的叶子;晾晒的衣物从生锈的铸铁栏杆上垂下来,衬衫、校服、老伯宽大的唐裤,在偶尔掠过的穿堂风里,飘飘荡荡,散发着阳光和皂角的干净气味。
随意在巷弄街市里溜达,路过一个菜市场,摊档上,各种鲜鱼像一排排金褐色的刀剑悬挂着,海腥气浓烈而霸道;旁边是水灵灵的蔬菜,码得整整齐齐;肉铺的老板叼着烟,手起刀落,利索得很。讨价还价的声音,用的是我半懂不懂的粤语,混着葡语单词的音调,成了一种独特的、只属于这里的市井交响。


路过一些老建筑或是葡式建筑,它们似乎还散落着历史庞大而苍凉的影子,轻轻覆盖在普通人温热的、市井的生活之上,两者彼此渗透,像茶与柠檬,调和成一种复杂难言又无比真实的安然。这座城,便在这份安然里,继续着她日复一日,东西交织的、平常的传奇。
在一处巷子口,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躲在墙角玩着手机游戏,我拍他们的时候,一个小孩子抬头与我的目光相遇,他调皮的眼神有趣又天真。


在这里的街道,一件与隔壁家晾晒的被子与锅里翻滚的云吞面一样,构成普通人生活背景的物件。历史与日常,在这里完成了一次无声的、也是最重要的交接——它不再是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年代与事件,而是生活中一道可供凝视的、温暖的风景。
在澳门逗留的时光,路过气势恢宏新葡京娱乐城,也走过威尼斯人灯火通明的娱乐场,也在澳门银河里走了一圈,那些光怪陆离的空间暗涌着深不可测的江湖,而我的兴趣在于市井。
在这座城市,运气是个中性词。有人把它兑换成筹码,有人把它寄托于神明,而我,只是喜欢在这座城市的时空缝隙里,偷得了一场充满市井喧嚣与这座城遥远的记忆。